七(第2/5页)
才不过一个月左右的时间,偏屋的样子就变得陌生了。虽然坏掉的门铃、煞风景的家具、任其荒芜的庭院都还是以前的老样子,可一脚才刚踏入,便感觉到不舒服。然而随即断定原因并不在平方根身上,也就暂时松了口气。他既没窒息也没触电,好端端地和博士并排坐在餐桌前,脚边放着双肩包。
我之所以感到不舒服,是因为在他们俩对面出现了主屋那位孀居老太太的身影。在她身侧,候着一位陌生的中年妇女。大概是继我之后派遣过来的保姆。记忆中理应只有博士和平方根和我三个人的地方,就因为横插进来两个不常见的人物,空气就被说不清道不明地搅得不和谐了。
刚松了口气,我就开始纳闷得不得了,平方根怎么会在这里?老太太就坐在餐桌的正中间,和面试时一样,还是一身雅致的装束,左手里也还是握着手杖。
平方根也不打算和我交流一下目光,只静静地坐着。博士坐在他旁边,呈正在思考的姿势,兀自将意识集中在和任何人的视线都不会交错的方向上。
“您这么忙还要把您叫过来,真是非常抱歉。来,请坐这边。”
老太太叫我在椅子上坐下。因为从车站一路跑过来,我这时还气喘吁吁,还没法好好说话。
“请坐,请不要客气,坐下吧。喂,你去给客人倒杯茶来。”
保姆进了厨房。不知道她是不是“曙光”的人。无论老太太措辞怎样客气,从不停舔嘴唇以及拿指甲在桌上刮来刮去的动作,还是看得出她情绪相当激动。我吃不准怎样寒暄才好,姑且依言坐下了。
沉默持续了半晌。
“敢问两位……”老太太一边更使劲地磨着指甲,一边开口说道,“是抱着怎样的想法呢?”
我调整好呼吸,回问她说:“请问——是我儿子做了什么不该做的事了吗?”
平方根耷拉着脑袋,反反复复把阪神虎的棒球帽在膝头捏瘪了又撑开来。
“请让我来问您一个问题。为什么已经辞工的保姆的孩子还有必要到我家小叔这里来呢?”
好容易涂好的指甲油剥落了,碎成粉散落在餐桌上。
“我没干坏事。”平方根低着头说道。
“你可是一个老早就已辞工的保姆的孩子。”
老太太打断了平方根的话。尽管她嘴里反复强调“孩子、孩子”,可却压根儿不愿瞥平方根一眼;她也没朝博士看一眼。她一开始就没当这一老一少在场。
“不是的,我想这不是有没有必要的问题……”我回答道,我还不明白具体情况到底是怎么回事。“我想他只是过来玩玩。”
“我从图书室借了《路·格里克(2)的故事》,想来和博士一起看。”平方根终于抬起了头。
“一个六十出头的男人和一个10岁的孩子在一起玩什么,你说?”平方根的话再一次遭到无视。
“我儿子事先没对我说,也没考虑到您是否方便,就跑来打扰,实在是非常抱歉。是我监管不力,非常对不起。”
“不,我不是要追究这个问题。我的问题是,尽管我们已经辞退了你,你却还是把孩子送到小叔这里来,你这样做是否怀有某种意图呢?”
指甲刮擦桌面的咯吱咯吱声逐渐变得刺耳起来。
“意图?您好像有点误会了。顶多是个10岁孩子呀,他是想玩就来玩了。因为找到了一本有趣的书,也想给博士看看。这理由还不够充分吗?”
“嗯,也许吧。孩子可能没有坏心。所以我想请问的是您本人的想法。”
“我只要儿子开开心心的就好,除此以外没什么奢望。”
“那你为什么要把小叔卷进来呢?你们晚上带着小叔三个人一道外出,还留宿照顾病人,我可不记得我曾经要求你做这种工作。”
保姆端来了茶水。她是一名安分守己的保姆,不插半句嘴,不发出一丝声响,只按人数依次放下茶杯。很显然,她不可能替我说好话。果然,她一副麻烦事可别牵连我的样子,飞快躲回厨房去了。
“我承认我是超出了工作范围。但是,我并没有什么意图或者企图,我的想法要单纯得多。”
“是为了钱吗?”
“钱?”听到如此意外的一个字,我不觉连声音都变了。“这话我不能当听过就算,何况还当着孩子的面。请您收回。”
“除此以外我还能怎么想?你就是在企图讨取小叔欢心,伺机骗钱。”
“荒谬……”
“照理你已经被辞退了。照理你已经和我们断绝关系了。”
“请您自重。”
“那个……”保姆再次露面了,她已解下围裙,手里拎起了包。“时间到了,请容许我先告辞了。”
和端茶出来时一样,她连脚步声也没有地走了,我们目送着她的背影离开。
博士思考的浓度越来越深重,平方根的帽子皱得不成样子了。我长长地吐出一口气,“因为是朋友吧?”我说,“来朋友家玩玩不行吗?”
“你说谁和谁是朋友?”
“我和我儿子,还有博士。”
老太太摇摇头:“我看您的希望可能要落空了。小叔没有所谓的财产。他把从父母那里继承得来的东西全部投进数学里去了,投进去以后一块钱也没收回来。”
“您这些话和我没关系。”
“小叔没有所谓的朋友,一次也没见他有朋友登门到访。”
“那样的话,我和平方根就是他最初的朋友。”
蓦地,博士起身说道:“不行!不准欺负孩子!”接着从口袋里掏出便笺纸,在上面写了些什么,然后把纸片搁在餐桌正中央,径自走出了房间。他的态度毅然决然,像是事先就已决定好了应该这样做似的。他没有生气,也不慌乱,一任静寂拥裹着他。
剩下的三人默默注视着便条,久久不曾动弹。纸上仅只写着一行算式——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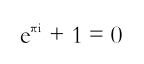
谁也没再多说一句闲话。老太太停下了刮擦指甲的手。看得出来,激动、冷漠以及狐疑等等正从她的眼眸里一点点地消退。我想,这是一双能够正确理解算式之美的人的眼睛。
不久,工会来了通知,叫我回博士家工作。原因不确定,不知是随访的结果,老太太的意向发生了变化,还是单单由于新保姆无法习惯,工会又安排不出合适的人手。无论如何,总之博士是敲到了第11颗蓝星星。至于加在我身上的那些毫无道理的误会是否已经消除,我无从确认。
思来想去,仍旧觉得老太太的抗议很不可思议。她通过向工会告密的形式解雇了我,又对平方根的到来作出那样夸张的反应,甚至可说是古怪了。